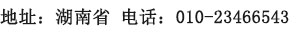回望姐姐的天空
文图/陆静
姐姐的来信就放在桌上,姐姐的全家福也摆在了桌上。信上姐姐说:“今年的民师转正考试我考了全校第一,全镇第七名,转正了。拍张照片寄给你。”照片上的姐姐从容自信,旁边站着她已上中学的女儿和丈夫,一派幸福安详。但她斑白的两鬓和额头的皱纹,分明镌刻着岁月的艰辛和沧桑。
姐姐是家里的长女。母亲常说:“小时候,你们姊妹几个就数你大姐乖了,她懂事、勤快,顾惜你们姊妹。”说着母亲的眼角就湿润了。五岁时,遇上三年自然灾害,多长时间见不着米粒,即便吃糠咽菜,姐姐也总把稠的留给弟妹们,自己喝汤。姐姐乳名叫“白妮”,长得皮肤细白,温柔可爱,是我们姐妹中最端庄美丽的一个。
六岁时,姐姐已放了一头大水牛,在村上每天挣八个工分了。阴雨天,山高路滑,姐姐从牛背上摔下来,头上至今还留下明显的疤。六岁时她就开始帮母亲干家务,烧火做饭,照顾弟、妹,是母亲的左膀右臂。十二岁时,姐姐见村上同龄的孩子都背着书包上学了,只有自己牵两头牛在漫地里跑,她怯怯地向母亲说:“我也要上学。”母亲看看她又看看父亲说:“去吧!”
放牛的姐姐姐姐聪慧好学,刻苦勤奋,她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,又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,并顺利地考到镇里唯一的一所中学里读初中。三年后,她初中毕业时已经十七岁。那时大队小学校里正好缺教师,她被推荐到小学校里做了民办教师。民办教师是农民,生产队里记工分,重要农活一样得干,如冬天挖树坑,开渠打坝的土石方一点不少地分到家里。白天,她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,放学后就直接去工地干活,从来没有说过苦和累。
父亲经常不在家,我和二姐及弟弟都在上学,光农活母亲一个人就忙不过来。生活上姐姐俨然成了一家之主。她总是很早就起来,做好饭把我们一一叫起,母亲也该下早工了。吃了饭我们随姐姐一起去学校。晚上,她除了备课外,总是坐在灯下缝缝补补,给我们纳袜子做鞋,二姐的裤子还没做好,弟弟脚上的鞋就已露“鸭蛋儿”了;她总也不闲着,做了这个的再做那个的。新衣服总是让着二姐穿,因为二姐个子高,二姐穿旧了大姐再改制改制自己穿。所以记忆中总也没有大姐穿好看的新衣服的时候。
做民办教师的姐姐母亲成天被地里的农活累得腰酸背疼,我们也已习惯了姐姐的关爱和照顾。不管缺少什么,我们只管朝她要,而姐姐都能变戏法一样满足我们的要求。姐姐给二姐扎的袜垫儿像工艺品一样漂亮,姐姐给我做的方口布鞋让全班的女生都羡慕不已。其实,姐姐总共只上了六年学,她边学边教,靠着自信和勤奋,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。
年,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,学校里的年轻老师都跃跃欲试。姐姐也报考了。她第一次走进考场,考完后,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,考试的内容大部分她根本没学过,大多是高中以上的知识,自己的程度考师范都有些吃力,她决定复习复习明年报考师范。她与本校的女同事一起报考,一起学习,准备考试。
即将走进考场的6月,母亲与村里人口角后突然患了精神病,又哭又叫地满村跑,吓得我们不敢进家门。傍晚,姐姐安顿好母亲,在麦秸垛旁找到我和弟弟,领回家里后哄着我们睡下,她开始给母亲熬药,准备着明天的家务事。父亲不在家,他正领着青壮劳力在很远的山里修水库。一个星期后,母亲的病仍没有好转,姐和父亲一起把母亲送到信阳的精神病院里治疗,医院照顾母亲。不到十天,我们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,姐领着我医院,与父亲一起把母亲接出来拉回家里。母亲却突然醒来,哭着要吃东西,在医院里可能是安定注射得过多的缘故吧,吃过后,她又昏沉沉地睡去,梦里仍然胡言乱语。一个亲戚来看母亲,告诉我们一个偏方,说死人的骨头能治这种怪病。在夜深人静时,一个人到荒山野沟里去找,只要看到有磷火闪亮,你就扑上去,用红单子盖住,抱起来就走。回来的路上不要与任何人讲话,到家后用铁锤敲碎水煎服即可。去找药的人必须是病人的至亲,儿子或女儿。二姐正在害痢疾,我和弟弟光听说就吓得汗毛倒竖,觉得这简直是没办法的事。死人的骨头并不难找,村子北边山沟里,解放前打过仗,死的人无数,埋都埋不过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雨水的冲刷,白生生的人骨随处可见。大白天,胆小的人走到那里都会吓出病来。大姐看看蓬头垢面的母亲,又看看浑身发抖的我们,对亲戚说:“我去。”我和弟弟“哇”地哭起来,抱住姐姐说:“不能去呀,大姐,那里有鬼。”父亲搂过我们说:“别怕,我和你表哥站在大堰埂上看着。”
许多年过去了,我仍不敢想象单薄瘦弱的姐姐孤身一人走向沉沉的黑夜,在鬼魅出没的荒沟野岭里寻找白骨时的情景,面对松涛阵阵中猫头鹰的哭泣和狼群穿行林间沟壑的心情。母亲服了姐姐寻来的“药”,病情真的一天一天好起来。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,变得虚弱而平静。
9月,学校里的女同伴接到了师范的录取通知书,来向姐姐辞行。姐姐看着仍然有些呆气的母亲,良久没有一句话。她送女友到村头,女友安慰她:“你别难过,明年你一定能考上的。”姐姐根本没有时间难过,学校开学了,由于老师暂时缺员,她一个人要上两个班的课,改近百人的作业。每天她都是跑步去学校,放学后又跑步回家里,然后拿起农具扑向庄稼地,或奔向开渠的工地,去帮助正在那里孤军奋战的父亲。那时,我和二姐都在镇里读中学,只有星期天才回家。夜幕悄然降临,寒风呼啸,而大姐和父亲却挥汗如雨,村子里的人都走完了,父亲督促姐姐收拾东西,姐却坚持把活干完再收工,因为明天还有任务,父亲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干不完一家六口人的任务。待到干完活收工回家已是月上三竿了。姐姐接过母亲端来的汤,只喝一口碗就掉在地上,头歪在桌边睡着了。紧张的生活,繁重的劳动,缺油少盐的日子,使原本清秀的姐姐越来越虚弱。不知从哪一天起,姐姐的脸变得黄胖起来,一天课上下来,小腿肿得像罐子一样粗,一按一个坑。直到那天她突然晕倒在教室里,医院,经检查诊断,姐姐患的是急性肾炎。医生说:“假如不及时治疗,会转成慢性肾衰竭和尿毒症,那就不好治了。”医院里一天也没待,只是取了些药就匆匆赶了回来,她边工作边吃药,从来没有因病请过一天假。晚上,姐姐仍睡得很晚,备完课开始改作业,改完作业开始啃高中课本。几何题一道道地做,文言文逐段地背,那情景让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发紧,像被抓住一样的痛。这时,教育局已发通知,民师转正考试已经开始。母亲的身体也逐渐好起来,能做些家务和较轻的农活了。
年,姐姐结婚。姐夫是个砖瓦厂的工人,俩人除了几床被子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外,几乎什么也没有。他们暂住在学校的一间房里,家徒四壁。姐夫每月工资二十八元,而民师工资已从六元涨到每月十二元,姐因身体不好,没有再要地,生活本来就紧张,加上怀孕生孩子,日子更加捉襟见肘。我高中毕业,在家里务农。我因扶不动犁哭,因按不动铡刀切不碎草哭,因锄不好地、搬不动石头还哭,还给母亲使性怄气。姐姐每个礼拜都来,干这干那从不闲着。一天,她对我说:“你还去学校读书吧,家里的农活由我和你姐夫来干。”听完姐姐的话,我放声大哭,这次像要把所有的委屈一下哭个干净。去学校念书已没有可能,只是从此不再轻易哭泣,像姐一样学会了用双手而不是用眼泪去面对一切。农闲时我开始读些闲书,用笔写些生活的体悟。收秋以后,母亲让我去看姐姐。天下着雨,姐姐的屋子里到处摆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,没有一片干爽的地方。姐抱着自己两岁的女儿叹气说:“什么时候能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住就好了。”我摸摸床上潮湿的被子,心里涨满酸楚,并暗暗许诺,一定要为姐姐写间不漏雨的房子来。临走时,姐从一本书里找出五元钱来,硬塞给我说:“拿去买些你爱看的书。”那五元钱我把它夹在笔记本里,几年来无论多么困难都没舍得花。直到我离开山村和姐姐,重新走进学校读书时,我用它买了一张去省城的火车票。
以后的几年里,姐姐参加了各种提高业务水平的短期培训,又参加了电大学习,每年的转正考试她都参加,每考每不中。因为一年比一年的难度大,一年比一年的新知识多,但她仍不放弃。临毕业的暑假,我回家看姐姐,见她更加憔悴不堪。她见了我很高兴地说:“我正盖房呢!”我随她去看房子,只见几堵墙立在那里,周围到处是土堆和乱草。我问,为什么不盖房顶?“没钱哪。”姐说,“等到秋天,你姐夫开了工资再借些就能结上顶了。”
说什么都没用,姐已结婚近十年,女儿都已上小学了,却没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住,更盖不起房子。我想起自己的许诺,几年过去了,我不但没有给她写出一片瓦来,生活上却不断地受她接济。返校后,我第一次出于功利的目的,找人联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,所得稿费四百六十元,一分不动地给她寄去。
姐姐很快来信说:“你寄的钱收到了,我们用它买了水泥板,又借些钱把房顶接上了。很快我们就能搬进新房子里住了。你姐夫感激得不得了,逢人就说,咱有个好心眼的妹妹,咱一辈子都得感激她哩!”
读着姐姐的信,我鼻子发酸眼睛发潮。穿越岁月重重的艰辛与苦难,姐姐所给予我们的我永远无法报答,而这区区四百元钱,姐姐却要终生感激,我实在羞愧难当。
时光流逝,光阴荏苒,生活中姐姐以她不屈的身姿,从容坚定地引领我们走过岁月的凄风苦雨,直到现在,并真切地告诉我们,既然苦难注定无法避开,那就选择坚强和自助。
回望姐姐的天空,几多拼搏,几多蹉跎感慨。想起任性使气的自己,以及不得其时、不得其地、不得其位的众生,我的心像揳入一枚钉子一样,变得凄紧起来。姐姐以她永不停息的脚步踏碎生活的苦难,给我们以深刻的生命体悟和人生感受。无论世事如何沧桑难料,只要我们以人的自尊、以爱心沉静地面对一切并承担一切,抱着“万分之一亿分之一成功的希望”全力以赴,就能走出生活的层层磨难,走进一个艳阳高照的美好明天。(完)
.7.21